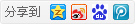線上提交翻譯需求
北大女作家與薩福之間的翻譯緣
時間:2012-07-07 06:18 來源:未知 作者:vikayau 點擊:
次
維吉尼亞·伍爾芙在某處談到,英語和法語的文學史上,最早泛起的都是一個女詩人。當然,後來,我們讀到的文學史,其中,男作家佔據了絕對多數的比例,而且,也好像與此相關,女詩人反倒成了稀有動物。這類稀有動物在由男性書寫的文學史上的命運大概有兩種,附庸,或是叛逆。比較而言,薩福則超出這兩重命運,成了一個被不斷重構或虛構的神話。
因為今人對古希臘社會文化歷史瞭解的有限,更因為薩福作品的散佚,關於薩福及其所糊口的時代的一切,後人的理解大多摻雜了想像的成分。人們樂於想像一個他們所需要的薩福,而他們的需要卻聯繫著他們最親身和最當時的願望——一種個人的和時代的限定性。詩人兼學者的田曉菲在其編譯的《“薩福”:一個歐美文學傳統的天生》(以下簡稱《“薩福”》)一書中,好像想要掙脫這種對於薩福的想像方式。一方面,她依據相對可靠的英語譯本,進行薩福的漢語翻譯;另一方面,在本書長長的“引言”中,她還側重考察或展示了歐美文學史上的一些詩人、作家和學者們對薩福的、各顯所需的重構。田曉菲所做的,大概可以稱之為一種拆解和重建並行,或者通過拆解來重建的工作,固然,後一種說法,用在建築學上,或許是行不通的。正因如斯,在本書的書名中,我們留意到,薩福是被加了引號的。
一旦有引號加諸其上,薩福便成了一個虛擬人物,或許我們不能夠用“她”(而只能用“它”)來指代這一個“薩福”了,由於它是一個傳統,是一個個被虛構出來的影像,作為插圖出沒在本書的書頁之間。所以,固然蘆紙殘片中的薩福支離破碎,但經由重構了的薩福並非一薩福,她是很多,是眾薩福。她不僅是上古時代一位偉大的女詩人,被柏拉圖譽為的“第十位繆斯”,而且她仍是一個強烈熱鬧的情人,一個“學問賅博的女子”,是母親和姐妹,是同性之愛的追求者,這在她的詩歌中體現得如斯充分,以致于到了現代,她被以為是女同性戀者們的守護神。在歐美文化史上,不斷有作家、學者根據個人與所處時代的需要,對薩福的身份認同進行詮釋和評價,而且,這些詮釋和評價話語之間經常佈滿了衝突和矛盾,它們致使我們間隔那個真實的薩福越來越遠了。它們簡直要令我們懷疑:存在一個真實的薩福嗎?關於這一點,田曉菲說得恰如其分:“由於‘薩福’是一個早就不再屬於薩福的名字和符號。‘薩福’和薩福的詩,沒有什麼關係。在這種情形下,我們惟一應該記住的是:假如沒有薩福的詩,‘薩福’也就根本不會存在。”當然,我想說,這不是我們惟一應該記住的,我們要記住的或許更應該是薩福的詩,如今,田曉菲版的這部薩福詩的漢語譯本正擺在我的案前,提醒我沿著薩福的詩句去“重構”一個我心目中的“薩福”。
薩福的詩最攝人心魄的元素,是她以一種直接、樸素、簡潔而又高貴的形式所傳達的激情。且讀她被公認的最聞名的兩首,即本書第一輯所選的第1和第15首。前者寫到抒懷詩的主人公向愛欲之神阿佛洛狄忒祈禱,“又一次”祈求女神幫她掙脫愛情帶來的苦痛和那份“強勁的重負”。全詩共7節,從第1節到第6節之間,有一個微妙的視角轉換,即由祈禱者“熱切祝求的聲音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女神阿佛洛狄忒的聲音”,因而,在這首詩的中間形成了某種聲音的雙重性,祈禱者的癡狂和對祈禱者的審閱,充分地傳達了深陷愛情苦痛之中的詩人的內心矛盾,既狂熱又理智,既失望又佈滿著但願的交織。對如斯複雜微妙的情緒波動,田曉菲沒有像別的譯者那樣,用引號把女神的聲音獨立出來,而是巧妙地恍惚了這種聲音轉換的痕跡,這就使詩的情緒更直接地呈現詩人的複雜心理變化。第15首描繪了陶醉在戀愛中的人的感慨感染。以愛中人身處三角戀情之中所感所想為主題的詩,大概算不上薩福原創,而且千百年來它也成了文學中的典範主題之一。然而,薩福的描繪卻能調動和買通一個閱讀者全身的感慨:“當我看到你,哪怕只有/一刹那,我已經/不能言語”“舌頭斷裂,血管裡奔流著/細小的火焰/黑暗蒙住了我的雙眼/耳鼓狂敲”“冷汗涔涔而下/我顫慄,臉色比春草慘綠”。誠如伍爾芙所言:“讀詩是一門複雜的藝術。大腦有良多層次,詩越是偉大,就有越多的層次高興起來,伎癢。它們好像也井然有序。我們讀詩讀第一遍時使用的是感官功能,開啟的是心靈之眼。”所以,或許分析薩福的詩是不必要的,只要我們直接反復地閱讀就足夠了,而在或長或短的、必要的“譯者注”之中,田曉菲也沒有對薩福名篇或殘章進行過多的讀解與評析,而是做了一些聯繫和比較的工作。這種更具學術色彩的工作反倒更切合於對於詩的閱讀和理解。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互文語境,不僅令我們意識到對於人類共通的情感,歷史上曾有很多詩人或作家都不約而同地以相似的風格表達過,而且,它也多少讓我們能夠相信“所有偉大的詩歌都由一人所寫”(博爾赫斯語意)這樣一種頗為禪玄的推斷。
《“薩福”》一書的第一輯中所選101首詩,是學者們公認薩福所作詩歌,而第二輯所收的12首,是學者們持懷疑意見的薩福詩作。兩輯的選詩,譯者均以選擇名篇和較完整的篇章為尺度。或許,這種稍加嚴格的、顧全完整性和正確性的,用田曉菲所說的“主觀”的選詩尺度,反倒更有助於我們領會一個完整的,雖不夠全面豐碩的詩人薩福。而所選殘詩中,空白的方框和它們旁邊的文字,奇妙地形成了一種相互映照的情境,換言之,對於薩福的詩歌,我們仍舊需要用想像去填充,她需要我們的再創造,由於她的詩歌體現出一種源頭性質。這麼說不單意味著,薩福的詩歌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和其卓越的藝術普遍性,而且,它也意味著,薩福詩歌所激發的,那個不斷由後來者“重構”的傳統中,有一部門是值得正視的。儘管在《“薩福”》的第三輯中——關於歐美文學傳統中從未間斷過的對薩福的再書寫,包括以之為題材和從她詩歌中汲取靈感與典故的寫作,田曉菲並未凸起這一點,但她所列舉的那些詩人中,卻有一半是女性。因此,我這裡要談到的,是由現代女詩人們致力開創的女性寫作傳統。
固然傳說中的繆斯們都是女神,加上薩福,總共有十位女性司職古希臘文藝,然而,在一本《古希臘抒懷詩選》(水建馥譯,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)中,我們唯讀到薩福一位女性的詩歌,其他31位均是男詩人。又傳說,薩福在勒斯波斯島上招收女弟子,向她們傳授詩藝和“愛的藝術”,甚至包括美容,可是,我們也沒有發現包括她在詩中提及的為她所愛的女子中,有一位曾如薩福一般以詩留名。這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情。豈非說,總體上比較,女性之詩才不及男性麼?豈非說,薩福有詩才,僅僅是由於她是那個“男子氣概的薩福”(古羅馬詩人賀拉斯語)麼?或者,甚至,是“薩福的性傾向”決定了她不斷被“重構”、“重讀”的可能麼?
所有這些迷惑,在我看來,它們已經並且正在被現代以來的女詩人們,當然也包括一些對女性書寫才能讚賞的男作家們破解。從《“薩福”》一書中,編譯者選取的歐洲第一位職業女作家克利斯蒂納·德·比桑(約1364-1429)的《夫人城》(節選)裡有關薩福的論述,我們便可以看出,女作家已經開始改寫由男性偏見織就的薩福話語。在她心目中,薩福是一位集美貌與才智於一身的“學問賅博的女子”,是不同詩歌題材的發明者,被視為最偉大最聞名的詩人之一。對薩福的評價既已發生一種性別話語的顛覆性變化,而另一方面,女詩人們從薩福詩歌中獲取靈感的例子則更其普遍。克莉絲蒂娜·羅塞蒂、愛米莉·狄金森、麥克·菲爾德、西維亞·湯森·華納與瓦倫汀·奧克蘭、H.D.、艾米·洛瓦爾、西維亞·普拉斯等歐美女詩人皆從薩福詩歌中獲取過營養。這種通過寫作延續女性書寫傳統的方式依然沒有終止,在一篇題為《強迫的異性愛和女同性戀的存在》的論文中,美國當代女詩人艾德里安娜·裡奇則試圖自覺地尋求一種女性書寫傳統,它隱秘地由被她稱之為的“女同性戀連續同一體”的某種文化氣力延續和傳承下來,正猶如“以薩福為中央的婦女學校中著名遐爾的‘女同性戀者’”以及其他一些婦女群體一樣。
希望此刻我們探討的話題不是簡樸地回到本文前面部門的有關“薩福的性傾向”的評判上,由於說到性別視角,在女作家之間確實存在一些隱約的聯繫關係性,它們觸動了女詩人寫作中相關的思維方向和自我意識,好比上文提及的薩福至於各位女詩人們,再好比勃朗甯夫人之于狄金森,簡·奧斯丁之於瑪格麗特·阿特伍德,薩福之于葡萄牙女詩人索菲亞·德·梅洛·布裡奈爾·安德森,當我讀到後者的詩句“啜飲月色/神游遠方”時馬上聯想到薩福……如何解釋這種女性作家之間的聯繫關係性,裡奇的方法不失為途徑之一種,固然不免偏狹,或許,我們可以嘗試拋卻身份認同的便捷路徑,從詩歌自身出發,去開掘存在於女性書寫者之間更其微妙複雜的精神聯繫關係性。而且在這一意義上,我們也將會擁有越來越多的“薩福的姐妹們”,或“莎士比亞的姐妹們”。
因為今人對古希臘社會文化歷史瞭解的有限,更因為薩福作品的散佚,關於薩福及其所糊口的時代的一切,後人的理解大多摻雜了想像的成分。人們樂於想像一個他們所需要的薩福,而他們的需要卻聯繫著他們最親身和最當時的願望——一種個人的和時代的限定性。詩人兼學者的田曉菲在其編譯的《“薩福”:一個歐美文學傳統的天生》(以下簡稱《“薩福”》)一書中,好像想要掙脫這種對於薩福的想像方式。一方面,她依據相對可靠的英語譯本,進行薩福的漢語翻譯;另一方面,在本書長長的“引言”中,她還側重考察或展示了歐美文學史上的一些詩人、作家和學者們對薩福的、各顯所需的重構。田曉菲所做的,大概可以稱之為一種拆解和重建並行,或者通過拆解來重建的工作,固然,後一種說法,用在建築學上,或許是行不通的。正因如斯,在本書的書名中,我們留意到,薩福是被加了引號的。
一旦有引號加諸其上,薩福便成了一個虛擬人物,或許我們不能夠用“她”(而只能用“它”)來指代這一個“薩福”了,由於它是一個傳統,是一個個被虛構出來的影像,作為插圖出沒在本書的書頁之間。所以,固然蘆紙殘片中的薩福支離破碎,但經由重構了的薩福並非一薩福,她是很多,是眾薩福。她不僅是上古時代一位偉大的女詩人,被柏拉圖譽為的“第十位繆斯”,而且她仍是一個強烈熱鬧的情人,一個“學問賅博的女子”,是母親和姐妹,是同性之愛的追求者,這在她的詩歌中體現得如斯充分,以致于到了現代,她被以為是女同性戀者們的守護神。在歐美文化史上,不斷有作家、學者根據個人與所處時代的需要,對薩福的身份認同進行詮釋和評價,而且,這些詮釋和評價話語之間經常佈滿了衝突和矛盾,它們致使我們間隔那個真實的薩福越來越遠了。它們簡直要令我們懷疑:存在一個真實的薩福嗎?關於這一點,田曉菲說得恰如其分:“由於‘薩福’是一個早就不再屬於薩福的名字和符號。‘薩福’和薩福的詩,沒有什麼關係。在這種情形下,我們惟一應該記住的是:假如沒有薩福的詩,‘薩福’也就根本不會存在。”當然,我想說,這不是我們惟一應該記住的,我們要記住的或許更應該是薩福的詩,如今,田曉菲版的這部薩福詩的漢語譯本正擺在我的案前,提醒我沿著薩福的詩句去“重構”一個我心目中的“薩福”。
薩福的詩最攝人心魄的元素,是她以一種直接、樸素、簡潔而又高貴的形式所傳達的激情。且讀她被公認的最聞名的兩首,即本書第一輯所選的第1和第15首。前者寫到抒懷詩的主人公向愛欲之神阿佛洛狄忒祈禱,“又一次”祈求女神幫她掙脫愛情帶來的苦痛和那份“強勁的重負”。全詩共7節,從第1節到第6節之間,有一個微妙的視角轉換,即由祈禱者“熱切祝求的聲音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女神阿佛洛狄忒的聲音”,因而,在這首詩的中間形成了某種聲音的雙重性,祈禱者的癡狂和對祈禱者的審閱,充分地傳達了深陷愛情苦痛之中的詩人的內心矛盾,既狂熱又理智,既失望又佈滿著但願的交織。對如斯複雜微妙的情緒波動,田曉菲沒有像別的譯者那樣,用引號把女神的聲音獨立出來,而是巧妙地恍惚了這種聲音轉換的痕跡,這就使詩的情緒更直接地呈現詩人的複雜心理變化。第15首描繪了陶醉在戀愛中的人的感慨感染。以愛中人身處三角戀情之中所感所想為主題的詩,大概算不上薩福原創,而且千百年來它也成了文學中的典範主題之一。然而,薩福的描繪卻能調動和買通一個閱讀者全身的感慨:“當我看到你,哪怕只有/一刹那,我已經/不能言語”“舌頭斷裂,血管裡奔流著/細小的火焰/黑暗蒙住了我的雙眼/耳鼓狂敲”“冷汗涔涔而下/我顫慄,臉色比春草慘綠”。誠如伍爾芙所言:“讀詩是一門複雜的藝術。大腦有良多層次,詩越是偉大,就有越多的層次高興起來,伎癢。它們好像也井然有序。我們讀詩讀第一遍時使用的是感官功能,開啟的是心靈之眼。”所以,或許分析薩福的詩是不必要的,只要我們直接反復地閱讀就足夠了,而在或長或短的、必要的“譯者注”之中,田曉菲也沒有對薩福名篇或殘章進行過多的讀解與評析,而是做了一些聯繫和比較的工作。這種更具學術色彩的工作反倒更切合於對於詩的閱讀和理解。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互文語境,不僅令我們意識到對於人類共通的情感,歷史上曾有很多詩人或作家都不約而同地以相似的風格表達過,而且,它也多少讓我們能夠相信“所有偉大的詩歌都由一人所寫”(博爾赫斯語意)這樣一種頗為禪玄的推斷。
《“薩福”》一書的第一輯中所選101首詩,是學者們公認薩福所作詩歌,而第二輯所收的12首,是學者們持懷疑意見的薩福詩作。兩輯的選詩,譯者均以選擇名篇和較完整的篇章為尺度。或許,這種稍加嚴格的、顧全完整性和正確性的,用田曉菲所說的“主觀”的選詩尺度,反倒更有助於我們領會一個完整的,雖不夠全面豐碩的詩人薩福。而所選殘詩中,空白的方框和它們旁邊的文字,奇妙地形成了一種相互映照的情境,換言之,對於薩福的詩歌,我們仍舊需要用想像去填充,她需要我們的再創造,由於她的詩歌體現出一種源頭性質。這麼說不單意味著,薩福的詩歌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和其卓越的藝術普遍性,而且,它也意味著,薩福詩歌所激發的,那個不斷由後來者“重構”的傳統中,有一部門是值得正視的。儘管在《“薩福”》的第三輯中——關於歐美文學傳統中從未間斷過的對薩福的再書寫,包括以之為題材和從她詩歌中汲取靈感與典故的寫作,田曉菲並未凸起這一點,但她所列舉的那些詩人中,卻有一半是女性。因此,我這裡要談到的,是由現代女詩人們致力開創的女性寫作傳統。
固然傳說中的繆斯們都是女神,加上薩福,總共有十位女性司職古希臘文藝,然而,在一本《古希臘抒懷詩選》(水建馥譯,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)中,我們唯讀到薩福一位女性的詩歌,其他31位均是男詩人。又傳說,薩福在勒斯波斯島上招收女弟子,向她們傳授詩藝和“愛的藝術”,甚至包括美容,可是,我們也沒有發現包括她在詩中提及的為她所愛的女子中,有一位曾如薩福一般以詩留名。這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情。豈非說,總體上比較,女性之詩才不及男性麼?豈非說,薩福有詩才,僅僅是由於她是那個“男子氣概的薩福”(古羅馬詩人賀拉斯語)麼?或者,甚至,是“薩福的性傾向”決定了她不斷被“重構”、“重讀”的可能麼?
所有這些迷惑,在我看來,它們已經並且正在被現代以來的女詩人們,當然也包括一些對女性書寫才能讚賞的男作家們破解。從《“薩福”》一書中,編譯者選取的歐洲第一位職業女作家克利斯蒂納·德·比桑(約1364-1429)的《夫人城》(節選)裡有關薩福的論述,我們便可以看出,女作家已經開始改寫由男性偏見織就的薩福話語。在她心目中,薩福是一位集美貌與才智於一身的“學問賅博的女子”,是不同詩歌題材的發明者,被視為最偉大最聞名的詩人之一。對薩福的評價既已發生一種性別話語的顛覆性變化,而另一方面,女詩人們從薩福詩歌中獲取靈感的例子則更其普遍。克莉絲蒂娜·羅塞蒂、愛米莉·狄金森、麥克·菲爾德、西維亞·湯森·華納與瓦倫汀·奧克蘭、H.D.、艾米·洛瓦爾、西維亞·普拉斯等歐美女詩人皆從薩福詩歌中獲取過營養。這種通過寫作延續女性書寫傳統的方式依然沒有終止,在一篇題為《強迫的異性愛和女同性戀的存在》的論文中,美國當代女詩人艾德里安娜·裡奇則試圖自覺地尋求一種女性書寫傳統,它隱秘地由被她稱之為的“女同性戀連續同一體”的某種文化氣力延續和傳承下來,正猶如“以薩福為中央的婦女學校中著名遐爾的‘女同性戀者’”以及其他一些婦女群體一樣。
希望此刻我們探討的話題不是簡樸地回到本文前面部門的有關“薩福的性傾向”的評判上,由於說到性別視角,在女作家之間確實存在一些隱約的聯繫關係性,它們觸動了女詩人寫作中相關的思維方向和自我意識,好比上文提及的薩福至於各位女詩人們,再好比勃朗甯夫人之于狄金森,簡·奧斯丁之於瑪格麗特·阿特伍德,薩福之于葡萄牙女詩人索菲亞·德·梅洛·布裡奈爾·安德森,當我讀到後者的詩句“啜飲月色/神游遠方”時馬上聯想到薩福……如何解釋這種女性作家之間的聯繫關係性,裡奇的方法不失為途徑之一種,固然不免偏狹,或許,我們可以嘗試拋卻身份認同的便捷路徑,從詩歌自身出發,去開掘存在於女性書寫者之間更其微妙複雜的精神聯繫關係性。而且在這一意義上,我們也將會擁有越來越多的“薩福的姐妹們”,或“莎士比亞的姐妹們”。